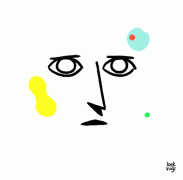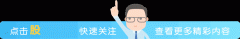时世平: 章太炎的汉语言文学观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期刊杂志社微信号:shnuxuebao
原刊于《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
作者 时世平/天津社会科学院《天津社会科学》杂志社副编审,文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语言文学研究。
内容摘要 晚清西学东渐,中学受到极大的冲击,作为文化发展序列中最为保守和滞后的语言,竟因为政治焦虑无法得到释解而被列入首要改革之列,以语言文字的兴废问题为核心的民族语言文字的变革,就摆在了其时知识群体的面前。章太炎基于其汉民族的历史文化观,以其小学修养为根底,提出了立场鲜明的保存汉字的汉民族文字观。以此为基础,他提出了“一返方言”的言文一致观,并基于小学的知识背景,对白话文学提出了批评,并对白话文学向雅精的深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一、 以汉文化为基础的民族主义汉字观
章太炎是一位极力主张语言文字重要性的民族主义者,但“从根本上说,章太炎是以文化,而不是以血统来定位中华民族的”。[1](P147)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中,章太炎提到,少读蒋氏《东华录》而觉得“异种乱华,是我们心里第一恨事”;俟读郑思肖、王夫之之书,“全是那保卫汉种的话,民族思想渐渐发达”。应该看到,此时的章太炎对民族主义的认识还处于感性阶段,在甲午中日战争后,在东西各国文化的影响下,章太炎才对民族主义有了学理性的体认,即以历史为根据来确认民族:“为甚提倡国粹?不是要人尊信孔教,只是要人珍惜我们汉种的历史。这个历史,是就广义说的,其中可分为三项:一是语言文字,二是典章制度,三是人物事迹。”[2](P1)章太炎进而指出:“今夫血气心知之类,惟人能合群。群之大者,在建国家,辨种族。其条列所系,曰语言、风俗、历史。三者丧一,其萌不植。俄罗斯灭波兰而易其语,突厥灭东罗马而变其俗,满洲灭支那而毁其历史。”[3](P323,P324)在后来开设国学讲习会时,章太炎在《民报》刊登的招生广告中,也强调指出:“吾闻处竞争之世,徒恃国学固不足于立国矣,而吾未闻国学不兴而国能自立者。吾闻有国亡而国学不无者矣,而吾未闻国学先亡而国仍立者也。”而该招生广告所要广而告之的,就是章太炎所讲之内容,即如上所讲的“中国语言文字制作之原”、“典章制度所以设施之旨趣”、“古来人物事迹之可以为法式者”。[4]因此,章太炎基于其小学修养,力倡以小学研究来达致国粹研究,“文辞的本根,全在文字,唐代以前,文人都通小学,所以文68章优美,能动感情。两宋以后,小学渐衰,一切名词术语,都是乱搅乱用,也没有丝毫可以动人之处。究竟甚么国土的人,必看甚么国土的文,方觉有趣。像他们希腊梨俱的诗,不知较我家的屈原、杜工部优劣如何?但由我们看去,自然本种的文辞,方为优美。可惜小学日衰,文辞也不成个样子。若是提倡小学,能够达到文学复古的时候,这爱国保种的原因是,不由你不伟大的。”[2](P8)章太炎将小学爱国保种复兴古学三者串联起来,高度认同汉民族及其文化,由是,在章太炎的理论思路上,小学就不再仅仅是简单的语言文字问题了“岂专引笔画篆、缴绕文字而已”,而是“国故之本,王教之端,上以推教先典,下以宜民便俗”。[5](P10)这一思想体认,贯彻章太炎的终身。在与《新世纪》派的论争中,章太炎又强调指出:“以冠带之民,拔弃雅素,举文史学术之章章者,悉委而从他族,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语言文字亡,而性情节族灭,九服崩离,长为臧获,何远之有?”[6]其对语言文字之于民族的重要性由是彰显。甚至到了其晚年,章太炎仍坚持文字是汉民族种性的载体,“文字亡则种性失”“夫国于天地,必有与立,所不与他国同者,历史也、语言文字也,二者国之特性,不可失坠者也。昔余讲学,未斤斤及此,今则外患孔亟,非专力于此不可。余意凡史皆春秋,凡许书所载及后世所添之字足表语言者皆小学。尊信国史,保全中国语言文字,此余之志也”。[7](P37)
在写于1902年的《文学说例》中,章太炎就开始强调文字对于语言的重要性,并提出了“世有精练小学而拙于文辞者矣,未有不知小学而可言文者也”。章太炎要以小学为根基,保全中国语言文字,由是他对文学作了全新的界定。在《文言总略》的开篇,章太炎指出:
文学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凡文理、文字、文辞皆言文;言其采色发扬,谓之。以作乐有阕,施之笔札,谓之章。……夫命其形质曰文,状其华美曰,指其起止曰章,道其素绚曰彰,凡者必皆成文;凡成文者不皆,是故榷论文学,以文字为准,不以彰为准。[8](P49,P50)
在章太炎看来,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文体各异,因此,只有追根溯源,从训诂文义方面入手,才能对之作出合乎中国实际的理论概括。在章太炎看来,文章是指有形质而自有“起止”。而“彰”则只指那些富于文采、藻饰和情韵的文章,它只是文的一小部分。因此,文章与彰是整体与局部的关系。具有文采和情韵的彰,一定属于文,但是,属于文的,却未必是彰。因此,界定文时,一定要抓住文的基本质素和规定性,也即“榷论文学,以文字为准,不以彰为准”。而且,在以后的一系列讲学中,他一直坚持自己对于文学的界说。在1922年曹聚仁整理的《国学概论》中,章太炎在上海公开讲学,也一再强调,“什么是文学?据我看来,有文字著于竹帛叫做‘文’”。[9](P49)试想当时的社会情境,正处于新文化与新文学运动风头正劲的时期,而章太炎却依然坚持自己对于文学的界说,可见他对于这种界说的认同。综观其后的表现,章太炎一生坚持未易。
章太炎认定文字是文学的根本规定性。文与不文的区别是文字,文字才是衡量文的根本标准。这样,章太炎对于文的致思路径明显表露出来:文以文字为标准,以文字为限。有字方为文,无字则不能算文。文不是语,不能形诸声音,而必须是“著于竹帛的文字”。由是,章太炎对于文的界定,既区别于口语形式的日常言谈,也完全不等同于以文采和情韵为标准的彰。“凡云文者,包络一切著于竹帛者而为言。故有成句读文,有不成句读文,兼此二事,通谓之文。局就有句读者,谓之文辞。”[8](P52)
在章太炎看来,文应该既包括用句读断句的文章,也包括不用句读断句的文字。“成句读文”涵盖“有韵之文”与“无韵之文”。“无句读文”则统括表谱、簿录、算草、地图等。“诸不成句读者,表谱之体,旁行邪上,条件相分。会计则有簿录,算术则有演草,地图则有名字,不足以启人思,亦又无以增感,此不得言文辞,非不得言文也。”[8](P52)章太炎强调,有无句读不能作为是否为文的评判标准,不能因为无句读断句,就否认无句读的篇章不是文,同理,有句读的文章虽然是文,但并不是文的范囿与全部,其实只是文的一部分。这样,章太炎就将文的范围大大扩展了。章太炎所说的文,包括一切用文字写成的东西,文学、科学、历史、文化、学术、文献等统统囊括在内,这样宽泛的标准,已经等同于我们今天所说的书面文化了。
更重要的是,在《文学论略》中,章太炎结合古代各种文类的具体发展与特点,把无句读之文单独归为一类,下设“表谱、簿录、算草、地图四科”,理由是它们用文字记载,虽然没有“兴会神味”,但却符合“有文字著于竹帛”的文的特质。同时,在成句读文中,章太炎将之分为有韵之文和无韵之文,其中,无韵之文分为六类,包括学说、历史、公牍、典章、杂文、小说;而有韵之文分为词曲、古今体诗、占繇、箴铭、哀诔、赋颂六类。值得提出的是,这种文的分类,把小说单独作为一类,突破了传统的经史子集的四库分类方法,表明章太炎对于小说在现代社会地位重要性的看重,提高了小说一向屈尊于历史中有稗于史的不入流的形象,打破了小说一向不能入文言传统的文学分类的传统做法,将以传统白话为表现形式的小说等诸文学形式纳入一向以文言为正宗的文学园地,使得文言与白话作为文学的表现两极,皆列为文学的园地,这种分类方法,以章太炎在其时的影响力和鼓荡,在某种程度上提高了小说的地位,更加完善了章太炎的汉字文化的兼收并蓄,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也启发了言文一致的民族语言的现代转型。
二、“一返方言”的言文一致观
众所周知,最早提出言文合一的人是黄遵宪,他在1887年的《日本国志学术志文学》中,根据西方的普世语文理论,提出了言文分合的问题。按照黄遵宪的说法,语言与文字的一致是必然趋势,而文字趋于简便便是语言克服言文相离的必然。因为,言文合一则行之弥广,言文相离则通文者少,则行之不远。而这种言文一致,又关系到民智的开化,进而又导向国家的强弱。因此,对于汉语而言,一定也会走如西方的言文合一的路径,使得“适用于今、通行于俗”,并且“明白晓畅,务期达意”,“令天下之农工商贾,妇女幼稚,皆能通文字之用”。他提出“我手写我口”,意在于强调言文合一,当然,这种言文合一,在黄遵宪的视域中,是指通用的语言接近口语,但并非专指白话。
言文不一,在中国历代有所显示。但这种言文分离真正成为问题的,却源于西方的传教士、外交官等。16世纪末到我国传教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注意到了书面语与日常生活用语的差别,并指出:“在风格和结构上,他们的书面语与日常生活中所用的语言差别很大,没有一本书是用口语写成的。一个作家用接近口语的体裁写书,将被认为是把他自己和他的书置于普通老百姓的水平。”“这样的情况更经常地发生在有文化的上流阶层谈话的时候,因为他们说的话更纯正、更文绉绉,并且更接近于文言。”①文言是社交用语,口语中的文言成分也很重,这是一种很不健康的风气。即使是晚清以提出“崇白话而废文言”而著称于世的裘廷梁的《论白话为维新之本》这样的以张白话而废文言的宣言式的檄文,却矛盾地以文言写成。此中意味,令人深思。这种言文分家的畸形现象直到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才受到根本冲击。“五四”新文化运动响亮地提出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的口号,从那时起,以现代口语为基础的白话文(即语体文)才开始取代文言文,成为中国人普遍使用的书面语,“言文基本一致”的现代书面语系统才告形成。
在西方言文合一的比对下,在西方物质文化的强力逼促下,对于言文一致的呼吁,时人多有所更张。康有为《大同书》中呼吁语言文字、语音“大同”;谭嗣同在《仁学》中力批中国语的繁难、费力甚至荒谬,呼吁“言文合一”。1908年,时任巴黎《新世纪》编辑的吴稚辉通过对比中西语言,根据西方语言学文字发展三阶段理论,提出既非拼音文字也非合音字的汉字是未开化人用的文字,因此,应当采用万国新语来取代与“科学世界”不相符的“野蛮”、“低效率”的汉语。吴稚辉认为,作为拼音文字的万国新语,“视形而知其字”,因而易学、易于推广。而且,对于以万国语代替汉语,在吴稚辉乐观的观念中,只要“私家则以新语著书,学校则以新语教授”,便能很快达到万国语一统世界而成为唯一语言的实际。显然,这种恨铁不成钢的爱国热情值得提倡,但是,这种废弃汉字而使得民族文化无根可立的民族虚无主义的思维逻辑却是不可取、不可行的。语言学家马建忠也以中国语言没有“葛朗玛”(grammar),因而难于学习,建议要向西方学习构筑文法,以使中国语言在使用上达到“经济”的原则。不管是对于中国语言的意气的抨击与抛弃,还是基于理论的经济原则的提倡,都说明了中国语言言文不一而不得不被抛弃、改造的命定运数。可以说,清末以来的文学现代性追求中,这种对于汉语的自卑与自虐一直都如影随形,未能摆脱。
在其时的语境下,要解决言文统一问题,有两种解决路径。一是以拼音文字代替汉字,一是以国语的制定求得言文的统一与国家的强盛。但各家具体操作又有所不同。在这一点上,劳乃宣的看法较有代表性地表达了其时持有两种言文一致观者的衷肠。首先,他指出了汉字本身的复杂性导致了其传播的受限。也就是说,中国文字渊懿浩博,义蕴精深,功用宏远,这一点上,为其他任何国家所不具备。但是,这种复杂性却使得汉字的接受受到限制,也就是说汉字非浅尝辄止所能习得,而是需要大量的学习时间,因此“能教秀世而不能教凡民”。这就使得汉字在言文一致的问题上表现出劣势来。泰西、日本等仅以二十字母,或是五十假名而使得言文一致。这有益于教育的普及,而教育的普及又使国家的强盛。这也是其时欲抛弃汉字而西化的典型理由。正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劳乃宣提出了阶段进行论。即,“欲文字简易,不能遽求语言统一,欲语言统一,刚必求文字之简易”。如何达到文字简易呢,就是“必各处之人,教以呼处土音,然后易学易记,即如旧日之字,变各处各以土音读之,不能皆用官音也”。劳乃宣注意到了汉字语音与文字的矛盾,并以方言作为突破口。即以方言作为学习官音的准备,即“先以土音学简字,于拼音之法,母韵声之理,已了然于胸矣。而官话母韵声之字与土音母韵声之字无异也,所异者音耳,以本识之字,本明之法,而但变其音,有不涣然易解者哉”。[10](P52)这一点,与章太炎的考虑有相似之处,但在教育上,又明显出现了其所指出的汉字难识难辨的怪圈。这种怪圈的打破,无论是对劳乃宣而言,还是对我们要述及的章太炎而言,都得依教育来实行。但教习汉字的时间长短与难易问题,在劳乃宣这里还是有待进一步商榷。章太炎并非仅仅局限于此,而是将这种观点与方法提到了实际操作的角度。
对于汉字的各种讨论,章太炎立足于自己的朴学基础与小学根柢,也即立足于汉字文化,对蔑视乃至废弃汉语的主张给予了批评。在《规〈新世纪〉》[6]一文中,他指出了语言文字的发展本身就有着不一致的因素在:“文字者语言之符,语言者心思之帜。虽天然语言,亦非宇宙间素有此物。其发端尚在人为。故大体以人事为准。人事有不齐,故言语之字亦不可齐。”而且,不同民族有不同民族的文化,不同语言承载了不同的文化蕴涵。因此,妄图以万国新语来取替不同文化不同民族所操持的语言,根本是不可能的语言实践。在章太炎看来,对于主张用万国新语者,其理由是欧洲各国文字的统一,但这种统一是本于其原始语言与所本语言的“无大差违,习之自为径易”的基础上,而汉字作为一种完全异质的语言文字,“至于转变语言,必使源流相当而后可”,因此,汉字很难也沿袭此种逻辑而使用万国新语。即使使用了万国新语,只能使汉字所记载的文化,以及语言文字之独异性消失殆尽。更严重的是,“若徒以交通为务,旧所承用,一切芟夷,学术文辞之章章者,甚则弃捐,轻乃裁灭,斯则其道大觳,非宜民之事也”。由引,也就失却去了言文一致的最初目的。
章太炎指出,相对于中国幅员广阔、交通隔绝、地域分散、文言繁杂的国情来讲,作为见形知意的汉字,其虽然“吐言难喻”,但“按字可知”的优势使其更能保持语言的统一与文化的绵延传承。如若以繁简来确定语言的优劣,汉字相对于泰西语言,在繁的方面完全占有优势,“故以此三十六者,按等区分,其音且将逾百,韵以四声为剂,亦有八十余音,二者并兼,则音母几将二百。然皆坚完独立,非如日本五十假名,删之不过二十音也。宁有二十八字之体文,遂足以穷其变乎?夫声音繁简,彼是有殊,非直新语合音之法不可单行,纵尽改吾语言以就彼律,抑犹有诘诎者,是何也?”再者,汉字“所以独用象形,不用合音者”,就在于“原其名言符号,皆以一音成立,故音同义殊者众,若用合音之字,将芒昧不足以为别。况以地域广袤,而令方土异音,合音为文,逾千里则弗能相喻,故非独他方字母不可用于域中,虽自取其纽韵之文,省灭点画,以相切,其道犹困而难施”。既然万国新语不适合中国汉字,那什么样的方案才是最佳选择呢?
在《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11]一文中,章太炎指出了《新世纪》诸人对象形文字的偏见,指出应该在保留汉字的前提下,通过改良来弥补其在学习、使用上的弊病。(1)增加汉字的简便性。“欲使速于疏写,则人人当兼知章草。”为什么呢?“要之,汉初文史,辞尚简严,犹以草书缀属,今之繁辞,则宜用草书审矣。大抵事有缓急,物有质文,文字宜分三品:题署碑三版,则用小篆;雕刻册籍,则用今隶;至于仓卒应急,取备事情,则直作草书可也。”也就是说,要使汉字简化,应该利用传统的草书,借助于草书字形的定型化,禁绝各种任意使字形笔画损益的现象,使汉字的笔画由繁趋简。这也增加了汉字易于书写的简便性。(2)增加易辨性。“若欲易于察识,则当略知小篆,稍见本原。”这样做的好处是增加汉字的易辨认性。因此,一定要熟悉汉字小篆,因为汉字是象形文字,“小篆诎曲,成书反易。且日、月、山、水诸文,宛转悉如其象,非若隶书之局就准绳,与形相失。当其知识初开,一见字形,乃如画成其物,踊跃欢喜,等于熙游,其引导则易矣”。“凡从鱼之字,不为鱼名即为鱼事;从鸟之字,不为鸟名,即为鸟事。可以意揣度得之。”因此,540小篆,为初教识字之门矣。借助于小篆,把握汉字初文或偏旁,就能达到“见字识义”的便捷。(3)鉴于汉字的难于认识问题,章太炎指出了汉字反语的缺陷,这种缺陷就是两字拼一音,如果所拼切之字难于辨认,就很难正确地切出。章太炎提出了解决方案,即制定了一套简便的注音方法,使识字者得以很方便地学会“审音之术”。这种注音方法,“纽文为三十六,韵文为二十二,皆取古文,篆、籀径省之形,以代旧谱,既有典则,异于乡壁虚造所为,庶几足以行远”。由是,采用注音方法和教学方法,儿童入学能有效快捷地学习汉字。
在批判汉字统一要用万国新语说的过程中,章太炎提出了以上举措。但是,以上举措的推行,只能免废除汉字之一时之危,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即使是注音字母的推行,也很难保证中国地域广大、各地文言歧异给语音统一和标准化所带来的困难。因此,作为朴学大师的章太炎,基于汉字的特点,从汉字的本音本义入手,以其小学家才有的胆略与智慧,提出了一返方言,以此来达到言文一致的目的。
在章太炎看来,不管是言文一致,还是文言一致,其实质都是追求一种书写文字与语言相谐和一致的理路。这种理路在一定程度上只关注书写语言如何“我手写我口”,强行将言文不一致的弊病归结于汉字本身,而在一定程度上放弃了对于声音、言语等方面的探求。“晚清主张拼音化或者主张白话化的文字改革者,其理论根基几乎皆是言文一致,即改变作为书写方式的文,迫其与言一致,建立以语音为中心的书写和文化传播系统。”[12]但在章太炎看来,这种做法最终只是强扭言使之与文一致,而放弃了对于声音、言语的执着追求。因而并非真正的言文一致。他指出:“俗世有恒言,以言文一致为准,所定文法,率近小说、演义之流。其或纯为白话,而以蕴藉温厚之词间之,所用成语,徒唐、宋文人所造。”主张白话者如此,主张汉字统一论者也难免此误。主张汉字统一者,虽然主张“选择常用之字以为程限,欲效秦皇同一文字”,在章太炎看来,这种做法还是与其他的言文一致观一样,只是导致以文压言,果真如此的话,则“非直古书将不可读,虽今语亦有窒碍不周者”,其实这会更“限制文字为汉字统一之途”的。[13](P319,P320)由于以上的考虑,章太炎对于言文一致的思考,就在从这种声音、言语层面下手,解决汉语言中言语与文辞的一致问题。
章太炎认为,那些主张中国言文一致的人,他们的立论点就是错误的。原因在于,中国根本不存在言文分离的问题,俗世上那些普通人能说但却无字可记载的现象,甚至各地方言歧异无字可循等问题不是因为汉字的言文分离,而是因为“士大夫不识字”造成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各地方言处处不同,俗儒鄙夫,不知小学,咸谓方言有音而无正字,乃取同音之字用相摄代”。章太炎从小学家的视角,将言文不一致的原因归结为俗儒鄙夫的不懂文字音韵之学。在章太炎看来,方言里保留了太多的古字,“今世方言,上合周、汉者众,其宝贵过于天球、九鼎”,“若综其实,则今之里语,合于《说文》、《三仓》、《方言》者正多。双声相转而字异其音,邻部相移而字异其韵”,这些变化了音韵的文字,在各地的方言中表现各异,才会造成言文不一致的问题。
因此,只有一返方言,“审知条贯”才能“根柢豁然可求”。在章太炎看来,解决言文不一致的最佳方案即一返方言。“果欲文言合一,当先博考方言,寻其语源,得其本字,然后编为典语,旁行通国,斯为得之。”在章太炎的设计思路中,通过“一返方言,本无言文岐异之征,而又深契古义……殊言别语,终合葆存”。细读《论汉字统一会》和《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两文,章太炎皆提及《新方言》,由此可见其对之的倾重。
章太炎的主张并非向壁虚构,作为精通音韵、训诂等小学的国学大师,章太多并且援引了大量的例音。由此可见其对方言的重视。为何如此?在章太炎看来:“中国方言,传承自古,共间古文古义,储蓄甚多,而世人不在双声相转、叠韵互变之法,至有其语而不能举其字,通行文字,形体不过二千,其伏在殊言绝语中者,自昔无人过问。近世有文言一致之说,实乃遏绝方言,以就陋儒之笔札,因讹就简,而妄人之汉语统一会作矣。果欲言文合一,必先博考方言,考其语根,得其本字,然后编为语典,旁行通国,斯为得矣。”[14]
三、章太炎的白话文学观
章太炎善作古奥的文字,这一点的确很有名。就连鲁迅、周作人等都承认,他们年轻时古奥的文笔就受到章太炎的影响。在1934年《集外集序言》中,鲁迅就说:“以后又受了章太炎先生的影响,古了起来。”[15](P4)再者,周作人在《〈点滴〉序》中,也讲到了这一问题:“我从前翻译小说,但受林琴南先生的影响,1906年住东京以后,听章太炎先生的讲论,又发生多少变化。1909年出版的《域外小说集》,正是那一时期的结果。”[16]这种结果是什么呢?就是鲁迅在1920年3月《域外小说集序》中说的,“我看这书的译文,不但句子生硬,‘诘讠屈聱牙’”。②再加之章太炎作为其时饮誉学林的古文经学大师,其古文经学的知识背景,以及对于白话的不同程度的批评,的确使人很难把他与白话正面联系到一起。鲁迅就曾在《名人和名言》中对章太炎“非深通小学就不知道现在口头语的某音,就是古代的某音,不知道就是古代的某字,就要写错”。[17](P373)提出过反驳。这就使得章太炎反对白话文的形象几成定论。许多数据都足以显示,章太炎确实反对过白话文,但是他也确实有多篇白话文作品流传下来,究竟他为何反对白话文?又如何反对?既然反对,又为何会写白话文?
1. 反对白话诗
就整体而言,章太炎是传统古文经学家,他的文字古奥,诘屈赘牙,也许是这个缘故,大家以为他崇尚文章的高古典雅,因此被判定“不免有恶新的成见”,③但章太炎反对白话一说还值得商检,这在后文中将提到。但章太炎对于白话诗的反对,却是确有其事的。曹聚仁在《新诗管见(一)》中记载,章太炎对新诗大加讥刺,既认为“清末诗家的作品不成为诗”,又指出诗向下坠落则成为近代白话诗。④章太炎在《国学概论》之《国学之流派(三)》中谈到:
诗至清末,穷极矣,穷则变,变则通,我们在此若不向上努力,便要向下坠落。所谓向上努力就是直追汉晋,所谓向下坠落就是近代的白话诗,诸君将何取何从?提倡白话诗人自以为从西洋传来,我以为中国古代也曾有过,他们如要访祖,我可请出来。唐代史思明(夷狄)的儿子史朝义,称怀王,有一天他高兴起来,也咏一首樱桃的诗:“樱桃一篮子,一半青,一半黄;一半与怀王,一半与周贽。”那时有人劝他,把末两句上下对掉,作为“一半与周贽,一半与怀王”,便与“一半青,一半黄”押韵。他怫然道:“周贽是我的臣,怎能在怀王之上呢?”如在今日,照白话诗的主张,他也何妨说:“何必用韵呢?”这也可算白话诗的始祖罢。一笑!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在谈到白话诗是地,章太炎所用的几个词汇:“向下坠落”、“夷狄”、“始祖”、“一笑”。这四个词汇串起来,其义是,诗向不好的方向发展就成为白话诗。白话诗虽然从西洋传来,但在中国古代的夷狄也曾做过,也可以算作白话诗的始祖了。而且,这是当一个笑话来讲的。由此可见,章太炎对于白话诗的态度,应该是排斥大于赞成。而且,据曹聚仁所见,章太炎反对白话诗,并将有韵为诗发展到极致,“以《百家姓》、《千字文》、《急就章》是诗,就是为了排斥新诗才引入内的”。⑤
对于白话文和白话诗的关系的理解,同样见于上海《申报》1922年4月16日所刊载的《章太炎讲学第三日纪》中:“文章之妙,不过应用,白话体可用也。发之于言,笔之为文,更美丽之,则用韵语。如诗赋者,文之美丽者也。约言之,叙事简单,利用散文,论事繁复,可用骈体,不必强,亦无庸排击,唯其所适可矣。然今之新诗,连韵亦不用,未免太简。以既为诗,当然贵美丽,既主朴素,何不竟为散文?日本和尚有娶妻者,或告之曰:既娶矣,何必犹号曰和尚?直名凡俗可矣。今之好为无韵新诗,亦可即此语以告之。”细析此段话语的表述逻辑,我们可从以下四方面来理解。
第一,文章之妙,在于表情达意(此就文章的应用方面而言),但如只就表情达意而论,则文言白话皆可。这也可从章太炎的讲演文辞中看出。不管是文言,还是白话,只要能够“辞达而已”,就都可以且来表达思想感情。所以,文言、白话本无特别的区分。第二,诗赋这一类有韵之文则另当别论。因为,诗赋这类“文之美丽者”,一定要表现出文采来,词藻丰富,韵味十足。章太炎要求诗赋必须有诗味、诗意,而这诗味、诗意就表现在讲究文体,如果词藻全不讲求押韵,诗赋并无文采可言,更何谈美丽。诗赋不押韵不能称之为诗,没有音节的美,也很难称之为诗。白话诗不押韵,就失去了诗味、诗意,便无文采可言。第三,新诗可以写,但不能写无韵的新诗。章太炎的所谓“无韵”,有不押韵和不讲究音节美两种意思。对于诗而言,押韵、音节美是其文体之必然要求。假若既不讲求押韵,也没有韵律美,只是一句一行,便也直呼其为诗,则世间之诗,便失去了其应有的“美丽”。在章太炎看来,无韵之诗,不美的诗,在文体属于散文,就不应强称之为诗,径称为散文好了。更有甚者,如果全然不讲求诗味、诗意,实际上便等同于一篇呆板的大白话,连散文也称不上,更甭说移之为诗了。第四,对于现代白话诗而言,鉴于现代汉语白话词汇很不丰富,文采也很不够的浅俗缺点,如果不适当借用古代的词藻,一味只求口语化、浅俗化,白话诗就很难能够写得姿采动人。
也就是说,章太炎不排斥白话诗,但不同意无韵以及无文采的所谓新诗。这与他对文学的认知有极大的关系。在《国学概论》的《国学之派别(三)》中,章太炎提到:“总之,我们要先确定有韵为诗、无韵为文的界限,才可以判断什么是诗。……诗以广义论,凡有韵是诗;以狭义论,则惟有诗可称诗。”章太炎在《国学概论》中讲《治国学之方法》,当讲到“辨文学应用”时,有一段精辟的述说:
文学可分二项:有韵的谓之诗,无韵的谓之文⑥。……凡称之为诗,都要有韵,有韵方能传达情感,现在白话时不用韵,即使也有美感,只应归入散文,不必算诗。日本和尚娶妻食肉,我曾说他们可称居士等等,何必称作和尚呢?诗何以要有韵呢?这是自然的趋势。诗歌本来脱口而出,自有天然的风韵;这种风韵,可表达那神妙的心意,你看,动物中不能言语,他们专以幽美的声调传达彼等底感情,可见诗是必要有韵的。“诗言志,歌永言,声依咏,律和声”,这几句话,是大家知道的。我们仔细讲起来,也证明诗是必要韵的。我们更看现今戏子所唱的二黄西皮,文理上很不通,但彼等所唱也能感动人,就因有韵的原故。[9](P15,P16)
他在该项演说中,又提到:
文有骈体、散体的区别……依我来看,凡简单叙一事,不能不用散文;如兼叙多人多事,就非骈体不能提纲。以《礼记》而论,同是周公所著,但《周礼》用骈体,仪礼却用散体,这因事实上非如此不可。《仪礼》中说的是起居跪拜之节,要想用骈也无从下手。更如孔子著《易经》用骈,著《春秋》就用散,也是一理。实在,散、骈各有专用,可并存而不能偏废。[9](P15,P16)
从前面两段文字,已很清楚可以看出章太炎特别强调诗与文的形式大不相同,一般文章也许可以不讲究“格律”,但诗则必须严守一定的规矩,对一个传统学者而言,即使有这样的一点坚持,也是合理的。林荣森指出,上面两段文字已经可以看出章太炎对于诗歌的评判标准:“诗必应用韵,而白话诗却不讲究韵脚,这是他所不能接受的。”这也是章太炎一再反对白话诗的原因所在。“但在散文方面,章太炎认为,文体的应用则是视需要而定的,骈散可并存而不能废偏,即使在古代也有白话文,但在应用上应能明白表达意思,自然巧妙,‘曲尽其力’。因为,有些文句或成语原就很简练明白,不必一味描摩白话,刻意避开典雅的文句,有时绕了一大圈,费了很多唇舌都还不见得说得清楚,如此就太不懂得应用白话文了”。[18]
2. 白话离不开文言
章太炎并不排斥白话文。因为在他看来,文言与白话都是用来表达的。因此,采用文言还是白话,取决于表达的需要。在辨文学应用或述文章源流时,章太炎对于骈散文白各有其定位。如上节所述,“文章之妙,不过应用,白话体可用也。发之于言,笔之为文,更美丽之,则用韵语”。同时,在《文学论略》中,章太炎也正如陈平原先生所指出的:“在一般人心目中,博雅而好古的太炎先生,应该是站在白话文运动的对立面才对。这一不假思索、脱口而出的结论,实际上经不起仔细的考辨。章太炎擅长博雅渊深的魏晋之文,确实与胡适之主张‘明白如话’大异其趣;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章不但没像林纾那样公开向新文化人提出挑战,也未见如严复般的背后讥笑,反而是在收到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赠书后,用白话写信作复,与其讨论有关庄周的评价问题。……最为关键的,还是取决于其史家的胸襟以及相当开放的文体观念。”⑦而且,对于这种“文章之妙,不过应用”的文各有体,章太炎在《文学论略》中也有谈及:“所谓雅者,谓其文能合格。……古之公牍,以用古语为雅,今之公牍,以用今语为雅……要在质直而已。安有所谓便俗致用者,即无雅之可言乎!……近世小说,其为街谈巷语,若《水浒传》、《儒林外史》;其为神怪幽秘,若《阅微草堂》五种,此皆无害为雅者。若以古艳相矜,以明媚自喜,则无不沦入恶道。故知小产自有雅俗,非有俗无雅也。公牍、小说,尚可言雅,况典章、学说、历史、杂文乎?”这种理论倡导与主张,就很好地驳斥了一般人的想像,即作为古文大师的章太炎,并不排斥用白话写章回小说。因为,在章太炎看来,“工拙者系乎才调,雅俗者存乎轨则”,与其“俗而工者,无宁雅而拙也”。
章太炎虽然不反对白话文,但是却对白话文有自己的认识,即白话未必能传达事实真相,有其局限性。在《白话与文言之关系》一文中,章太炎概括了白话与文言的关系:“今人思以白话易文言,陈义未尝不新,然白话究竟能离去文言否?”并进一步认为:“白话亦多用成语,如‘水落石出’、‘与狐谋皮’之类,不得不作括弧,何尝尽是白话哉?且如勇士、贤人,白话所无,如欲避免,须说好汉、好人。好汉、好人,究与勇士、贤人有别。元时征求遗逸,诏谓征求有本领的好人,当时荐马端临之状曰:‘寻得有本领的好人马端临。’(见《文献通考序》)今人称有本领者曰才士,或曰名士,如必改用白话,亦必曰寻得有本领的好人某某。试问提倡白话之人,愿意承当否耶?以此知白话意义不全,有时仍不得用文言也。”在章太炎看来,白话文中常会夹杂成语,若干意思表达如能善用成语,则使文字显得简洁精妙,似乎没有必要刻意避开成语不用,而改以白话形容。他所举出的这类成语或字词,有时不仅不必刻意避开,甚至根本找不到更合适的白话来取代,因此他以为白话文仍无法彻底摆脱文言的使用。此一观念基本上是合理的,因为在胡适的看法中,亦非全盘排斥文言的使用,他认为白话中有合用的就尽量用白话,如白话有不足之处,则可用文言来补助,他在《文学改良刍议》中说“我们可尽量采用《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外史》、《红楼梦》的白话,有不合今日用的,便不用他;有不够用的,便用今日的白话来补助;有不得不用文言的,便用文言来补助”。[19]由是,章太炎断定:“以此知白话意义不全,有时仍不得不用文言也”;“白话中藏古语甚多,如小学不通,白话如何能好?”⑧
正是出于这种考虑,章太炎认为,白话离不开文言。理由如下:
其一,古之白话与今之文言难以区分。作为小学家,章太炎对白话文不仅有一番独到的见解,他还对白话文的历史与发展也颇为熟悉。章太炎指出,“白话文言,古人不分”。白话与文言之别,仅在于修饰与不修饰而已。白话在古代大都是“语录体”,例如尚书的诏诰,汉代的手诏,都可算是当时的白话。古代许多口语方言,虽为当时之白话,但在现今看来和文言又无二致,章太炎说《世说新语》所载:“阿堵”,“宁馨”,即乃当时白话,然所载尚无大异于文言,这样的字眼确实看不出有何白话性质,另如“《传灯录》记禅家之语,宋人学之而成录,其语至今不甚可晓”。所以古之白话与今之文言实难彻底划分。
其二,欲作白话,更宜详识字。章太炎认为,“昌黎谓凡作文字,宜略识字。学问如韩,只求略识字耳,识字如韩已不易。然仅曰略识字,盖文言只须如此也。余谓欲作白话,更宜详识字。识字之功,更宜过于昌黎”。为什么会有此问呢?这就显现出章太炎的见识了。在章太炎看来,现在的白话文提倡者,“以施耐庵、曹雪芹为宗师,施、曹在当日,不过随意作小说耳,非欲于文苑中居最高地位也,亦非欲取而代之也。今人则欲取文言而代之矣,然而规模、格律,均未有定。果欲取文言而代之,则必成一统系,定一格律然后可。而识字之功,须加昌黎十倍矣。何者?以白话所用之语,不知当作何字者正多也。今通行之白话中,鄙语固多,古语亦不少,以十分分之,常语占其五,鄙语、古语复各占其半。古书中不常用之字,反存于白话,此事边方为多,而通都大邑,亦非全无古语”。
再者,“白话中藏古语甚多,如小学不通,白话如何能好?且今人同一句话,而南与北殊,都与鄙异,听似一字,实非一字,此非精通小学者断不能辨”。从实际操作过程来看,章太炎指出:“古人深通俗语者,皆精研小学之士。”而今人不学小学,误读“为纟希为”作为“为希为谷”,而悍然敢提倡白话文,这在章太炎看来,是非常不确当的做法:“以颜氏祖孙小学之功如此,方能尽通鄙语,其功且过昌黎百倍。余谓须有颜氏祖孙之学,方可信笔作白话文。余自揣小学之功,尚未及颜氏祖孙,故不敢贸然为之。”
然而,章太炎此种言论受到当时人的攻击,甚至其弟子鲁迅也曾经批评章太炎,认为章氏“把他所专长的小学,用得范围太广大了”。[20]但是,我们不得不注意一个问题,对于在白话占据主流地位的1935年4月,章太炎对白话提出了批评,而不是在文白新旧尖锐对立的五四时期批评白话,是有其深层意义的。很可能是基于其“救学弊”的策略选择。这一点,陈平原先生指出:“一贯特立独行、喜欢语出惊人的太炎先生,其实并不卤莽行事。比如,首次公开批评新式学堂的《与王鹤鸣书》撰于1906年,便绝非偶然。早年也曾极力主张废科举兴学堂,可一旦清政府诏准自丙午(1906)科起停办科举,太炎先生便转而挑剔起新式学堂的诸多弊病。如此永远地‘不合时宜’,与其奇特的论学思路有关:虽然,学术本以救偏,而迹之所寄,偏亦由生。不相信凝固不变的事物或学理,对任何‘救弊’之举都保持必要的警惕,防止其成为新的‘独裁’若依这一思路,1930年代的中国,也该切实反省已成‘文学必用之利器’的白话文。不否认章氏‘救学弊’时,过于卖弄自家专长,因而效果适得其反;这里所要分辨的是,不该因此文而将太炎先生送入白话文反对派的行列。”[21](P194,P195)
综上,章太炎对于白话,并不是如人们所表面认为的持反对态度,而是认为白话应该在浅俗的追求中,更应该增加一点知识底蕴,也就是白话文的雅化与精致化。而这种对于白话的雅化与精致化追求,就是白话文运动以来,一直缺少的对于白话浅而欲的纠偏。语言变革虽经百年历程,但作家作品的语言愈显贫瘠,现代语言的粗鄙低俗与百年的语言变革有莫大关联,本文通过章太炎汉语言文学思想的爬梳,旨在以此为鉴,倡导一种表现精神追求的文学语言实践。而这,也正是汉语百年文学历程以来,一直高倡要用白话再造一种精英语言应该努力的方向。
注释:
① 参见《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江蓝生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46页。
② 《域外小说集序》,(署名周作人译),《鲁迅全集》第十卷,第177页。
③ 劭力子在《志疑》中谈到了章太炎的恶新,意谓承认古代的《尚书》等为白话而不承认现代白诗,因此而据以判断章太炎“不免有恶新的成见”。载章太炎《国学概论》附录,第73页。
④ 载章太炎《国学概论》附录,第80页。
⑤ 载章太炎《国学概论》附录,第80-81页。而章太炎只从有韵无韵区分诗与非诗,“以广义言,凡有韵者,皆诗之流。……《百家姓》然,《医方歌诀》亦然。以工拙计,诗人或不为,亦不得谓非诗之流也”。(《答曹聚仁论白话诗》)这是一种只形式不重内容的偏颇。把《百家姓》、《医方歌诀》也认作诗,这是对诗的一种片面的认识。诗既要有诗的形式:韵律、节奏,也要有诗的内容。
⑥ 对于此结论,曹聚仁有不同的意见,认为诗文是同源的,情意作用发达的是诗,理智作用发达的是文。因为文是多含理智作用,所以文大概是含解释申述种种情形,而诗多含情意作用,所以诗大多是感慨幽扬而含蕴不全露的。因此,判别诗文之别决不可专重有韵无韵的。参见曹聚仁《新诗管见(二)》,载章太炎《国学概论》附录,第85-88页。
⑦ 陈平原:《章太炎的白话述学文体》,载夏晓虹、王风等着《文学语言与文章体式从晚清到“五四”》,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92页。兹引回信内容之一段,如下:“适之你看。接到中国哲学史大纲。尽有见解。但诸子学术。本不容易了然。总要看你宗旨所在。才得不错。如但看一句两句好处。这都是断章取义的所为。不尽关系他的本意。仍望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⑧ 事实上,五四时期的白话“夹生半熟”可能正是它的特点,以明清笔记加上英式散文,成为时尚之文体。
参考文献:
[1]张汝伦.现代中国思想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2]章太炎.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A].章太炎讲演集[C].马勇,编.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4.
[3]章太炎.书哀焚书第五十八[A].章太炎全集(三)[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4]章太炎.国学讲习会序[Z].民报,第7号,1906-09-05.
[5]章太炎.小学略说[A].国故论衡[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6]章太炎.规《新世纪》[Z].民报,第24号,1908-10-10.
[7]章太炎.章太炎生平与学术[M].北京:三联书店,1988.
[8]章太炎.文学总略[A].国故论衡[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9]章太炎.国学概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10]劳乃宣.《重订合声简字谱》序[A].清末文字改革文集[C].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58.
[11]章炳麟.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M].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57.
[12]彭春凌.以“一返方言”抵抗“汉字统一”与“万国新语”[J].近代史研究,2008,(2).
[13]章太炎.论汉字统一会[A].章太炎全集(4)[C].
[14]章太炎.博征海内外方言告白[Z].民报,第21号,1908-06-10.
[15]鲁迅全集(第7卷)[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16]周作人.《点滴》序[A].点滴(新潮社丛书第三种)[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20.
[17]鲁迅.鲁迅全集(第6卷)[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18]林荣森.章太炎白话文学初探[J].通识教育年刊,2003,(5).
[19]胡适.文学改良刍议[J].新青年,1917,2(5).
[20]鲁迅.名人和名言[A].鲁迅.鲁迅全集(第6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21]陈平原.章太炎的白话述学文体[A].夏晓虹,王风,等.文学语言与文章体式从晚清到“五四”[C].合肥:安__________徽教育出版社,2006.

http://xuebao.shnu.edu.cn/
查看评论 回复
"时世平: 章太炎的汉语言文学观"的相关文章
- 上一篇:猴年春晚语言类节目"老咖"多
- 下一篇:第一个 C 语言编译器是怎样编写的?